作者: 发布时间:2024-06-11 来源:澎湃新闻+收藏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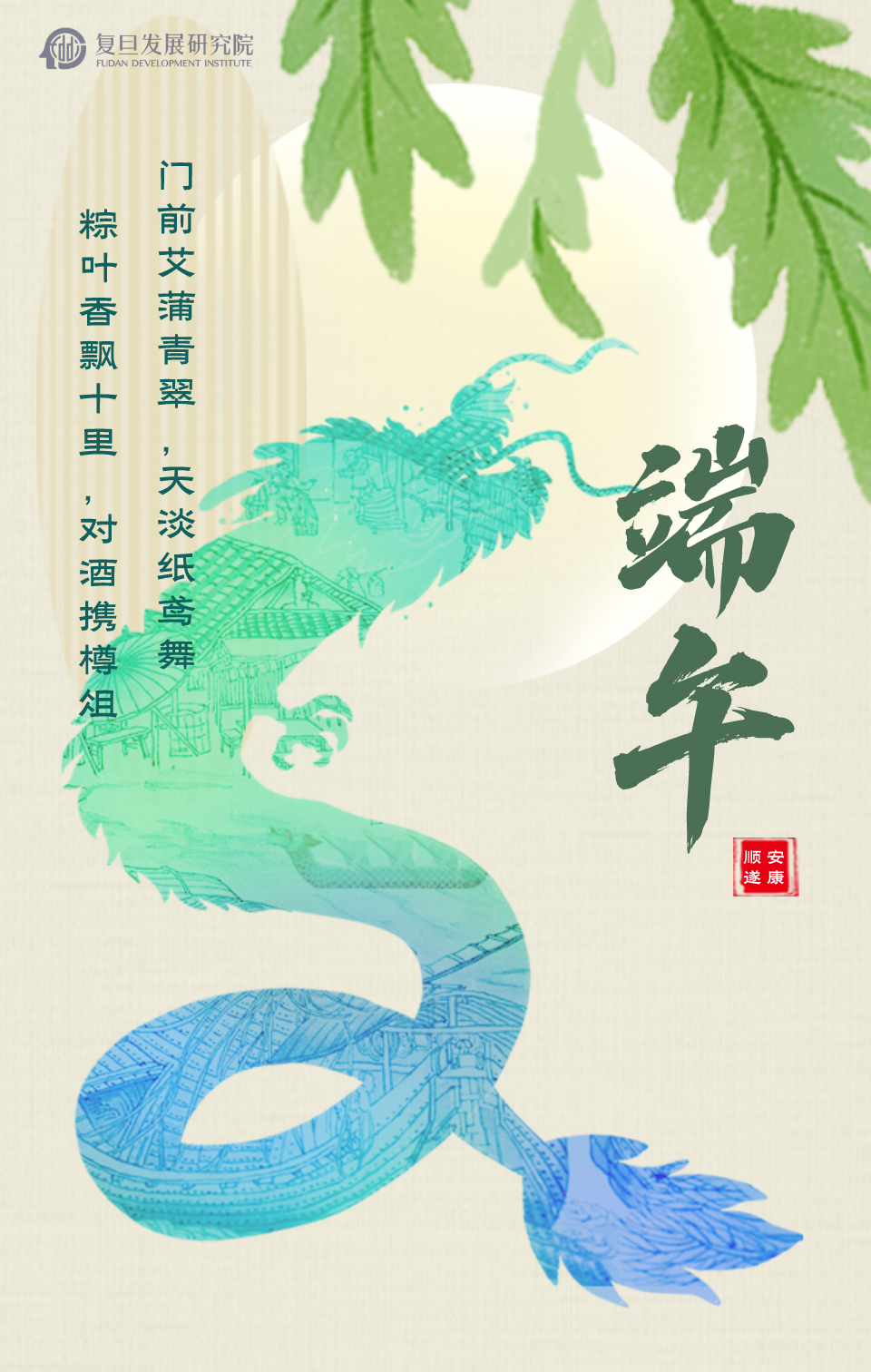
端午是粽叶飘香、满眼佳肴的时节💆🏽♀️,不由得令人想起种种美食👨🏽👼🏽。究竟什么是美食?那真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千差万别😄。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人群都有各自的美食谱系🤵🏽♀️。年近八旬🙎🏻,国内外的所谓美食我尝过许多🍗,但真正让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从心底里挚爱的美食,都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至今想来都感觉唇齿留香🧜🏻,垂涎欲滴。

文 | 李良荣 富达注册新闻学院教授,富达平台高级顾问
芋头蘸蟹酱
芋头蘸蟹酱,宁波农村的一道土菜💂🏽♀️。这道土菜让我念念不忘👩🏽💼,不仅仅是味道独特,非常鲜美,更因为那特别的年代。
1955年春📌,那时我十岁,母亲领着我们兄妹生活在宁波的小山乡。当时我们户口都在上海👧🏿,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每月到柴桥镇上买粮挑回家👰🏽♀️,在小山村独此一家。我不知道我们家每月有多少斤口粮,只知道我们必须搭配粗粮,比如山芋、土豆⚈、南瓜⛏,才能填饱肚子。那年秋天的星期日,母亲突然吩咐我:“你们去海涂上提些沙蟹来。”我满口答应,有老母亲吩咐,就有充分理由去海涂疯玩了!我约上小伙伴朝海涂飞奔而去。
我的家乡小山村离海很近,翻过一道小山岗🦐,再走一公里就到海边♦︎,一条一千米左右的海峡,对面就是大榭岛。大榭岛现在成了全国著名的产业园区🌎,那时只是一座贫瘠的小海岛。记得我就读的山门小学组织学生去春游,去过大榭岛,和当地小学搞联欢🏋️♂️,还办了篝火晚会。我第一次坐着小舢板渡过海湾🥢,看到一群水母在水中飘荡🤹🏻♀️,玲珑剔透,一张一合🟫。我惊讶于水中还有如此奇妙的生物🛤👩💼。
我们一到海边就呼啸着冲进海涂。我们家乡的海滩不是沙滩,而是泥滩🔌,很平缓😩,退潮后延伸几百米。海涂上到处都是小海鲜,最珍贵的是跳跳鱼,远远看上去有很多,但一走近,跳跳鱼一蹦一丈远,我一条都找不到。我见过渔民用钩子抛出去抓跳跳鱼🥿,也是十抛九空。海涂上最多的就是沙蟹,除了公蟹的大钳子有些粉红色⛷,全身灰色➖,两厘米见方。过去我们来海涂🏂,不抓沙蟹🕵🏻♂️,它没多少肉🫃🏿🤸🏽,不好吃;抓得更多的是蛤蜊、蛏子👨🏼🌾、小海螺,它们容易抓,用脚在海塗上踩🛍,踩到了顺手就抓起来👩🏻🦽,回家用咸菜煮,又鲜🫷🏼,肉也多👔。这次老母亲吩咐抓沙蟹🌵,不知做什么🙇🏽♀️,心想可能秋天到了👍🏿,沙蟹也肥了👀,我就奋力去抓吧👩🏻🔧。看上去🧩,沙蟹爬满海涂,但真要抓住也不容易🌃⚾️。人一走近,沙蟹快速钻进泥洞,我得把整条胳膊伸进泥洞里才能抓到。手一伸进泥洞,泥浆就喷出来🐽,脸上🫅🏿、身上全是泥浆,好在沙蟹实在多👩🦯,不到一小时就抓了五六十只。
回到家👩🏻,母亲很高兴👨💼,用清水冲洗干净⇾,再把沙蟹腌了起来。三小时后取出🧗🏿♂️,再把沙蟹身上不能吃的,例如后盖👳🏻、蟹鳃等等清理掉。母亲领我到邻居家,借用小石磨,把沙蟹磨成浆👜,而且要三磨,磨成稠稠的沙蟹酱。
那天傍晚,我母亲带我和兄弟几个去一块自留地上挖芋头👨💻。我家祖上在柴桥镇上做小买卖🏋🏽,没有水田,只在东山脚下有两垄自留地🖕🏽,东山山腰上有两块半亩大的山地🤶。那年春天,母亲带我们兄弟几个用草木灰拌粪作为两垄自留地的底肥🧕🏽,过了半个月的样子🆖,一垄种上芋头,一垄种上毛豆,芋头大概有20多窝💆。每隔一两个星期我会去巡查一番,看着它们出苗、生枝♟、长叶,慢慢长大🎖、长壮,终于到收获季节。在我们老家,芋头不是一次性全挖,而是吃多少挖多少👩✈️,可以延续一个多月🪹。那一次我们只挖了两窝芋头,就装了两筐。晚上🧑🏽🌾,母亲没有煮饭🙎🏻,用芋头当饭。热气腾腾的芋头端上桌🧀,母亲给我们一人一小碗蟹酱🕡。扒掉芋头皮,一口咬下去⤵️,粉粉的✴️,有点甜,像后来吃的糖炒栗子🙇🏻♀️,这大概就是我们老家人说的“栗子芋头”。芋头沾上蟹酱⛔️,蟹酱的咸鲜,芋头的粉香😿,沁人心脾。我感觉,我鼻子呼出来的气都是甜的,香的👱🏽♀️。
后来📚,芋头蘸蟹酱一直在我家的美食谱上🫵,但再也没有第一次吃的那么有滋味了🫱。或许那是我老母亲亲手酿制的🦵🏽,或许我参与了这道菜的制作。
芋头蘸蟹酱🪐,天下绝配。

葱烧大排
葱烧大排🙍🏽,现在是上海人的家常菜,是我一生所爱🤡。然而,回想我第一次看到葱烧大排,心头总会涌上难言的苦涩。
那是1961年初,我母亲烧给我哥吃的。我哥1959年报名去宁夏石嘴山钢铁厂当工人。1961年1月中旬,第一次回上海探亲,在家住了十来天后,要回石嘴山上班。老母亲问他:“明天你要走了🗂,想吃什么🏊🏻♂️?”我哥吞吞吐吐地回答:“就想吃一次葱烧大排。”1961年前后的那几年,除了空气,样样都凭票供应,但纵使有票,也不一定能买到大排。如果早上7点左右去菜场,除了菜皮🖖🏽,什么都没得剩下了👨,吃大排⛹🏻♂️?有点异想天开👩🏻🎨。我真不知母亲该怎么办。只见母亲愣了好一会儿,才含含糊糊说“看看能不能买得到”。晚上,待大家都睡了🦷,我还在孤灯下读书。母亲悄悄对我说🤞🏻:“今晚早点睡,夜里跟我去菜场🏭🎍。你哥这一去两年,下一次又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母亲的眼泪已掉下来,说不下去了。
那夜凌晨3点,母亲轻轻把我推醒,悄悄出门去菜场,花衣街的露天菜场🦸♀️。那一刻🛰🫵🏿,整个菜场就母亲和我两个人,母亲排在猪肉摊前🏃♀️,我排在鱼摊前🚞🥯,都排在第一位,寸步不敢离开,怕被人挤走🧖🏽🚊。过了半小时,才有人陆陆续续来排队。那是数九寒冬的凌晨🤾🏽♀️🫐,寒风凛冽👩🏼🦳,我感觉身上穿的棉衣像片薄纸🏃♂️,双脚麻木,只能不停跺脚。直到清晨5点半左右,肉摊👩💻、鱼摊终于开张👰🏼♂️。凭鱼票,我买到几条带鱼和小黄鱼🧛🏽,母亲竟意外买到两块大排。回家路上母亲满脸喜悦👰🏿♂️,不停地说:“你哥有口福啊,肉摊上总共只有六块大排,那个卖肉阿哥还说半个月来头一回卖大排。”我哥是下午6点火车👨🏿🍼,下午3点就得从家里出发。中午🤑,母亲在公用的厨房里烧大排,我想看看葱烧大排是怎么烧的,但看到一半我就离开了🧘🏿♀️,我看到母亲一边烧大排,一边不停地用手绢擦眼泪。看着母亲的伤心,我眼眶也湿了👱🏼♀️。午饭时我和弟妹都在外间,只有我哥一人在里间,我闻到了葱烧大排的浓烈香味。
我第一次吃上葱烧大排是1963年9月考入富达注册后🤾💪🏽。开完新生入学典礼会👇🏼🧑🏼🌾,我们去食堂吃午饭。正式成为大学生后的第一餐,午饭就吃上了大排💂🏼。捧起瓷碗里的大排🧑🏽💻,闻了又闻,好香啊🧖♀️,多年的美梦成真,心里乐滋滋的🌀。但刚刚咬了几口📏🦇,突然想起两年前母亲烧大排的情景🏋🏼♀️🤞🏻,眼泪不争气地“扑扑”掉下来,掉在大排上⛹️。怕让同学看到,我赶紧和着泪☝🏼,将大排吞下。我本以为可以经常吃到大排,其实,在当时富达平台食堂吃上大排也是难得的🐰。当年学生是凭饭卡吃饭,三餐供应都是统一配置🧑🏽⚖️。学生伙食费每月9元,每天0.3元🈺。一块大排的价格是0.15元,一个月能吃上两次就不错了👶🏽,吃大排对大学生也是难得的美味。但无论如何,我能吃饱饭了,不再有饥饿感,每天还有鱼、有肉吃。大学五年,我身高从168厘米长到173厘米,这是我大学期间的一大收获。
当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当教师(1982年),葱烧大排成了我的家常菜💆。到1990年代🧔♀️,我指导的研究生常来我家聚餐🤾🏼♀️。聚餐会维持了25年,葱烧大排是聚餐会的标配,一次烧二三十块,不管烧多少🧑🤝🧑,上桌一扫而空👨🏼🦰。不知是故意夸我还是实践了这么多年真的烧得特别有风味🛖,学生们怂恿我去五角场开一家“李教授排骨店”,说是保证生意兴隆。
葱烧大排,伴着我的伤感和愉悦。

面条起源于中国,已有数千年的食用史🧑🧑🧒🧒,种类繁多🧘🏿♂️,目前有记载的种类已达1200余款♦︎。以我的经验,阳春面是其中制作最简单的一种,就是把面条煮熟,加一勺油炸的葱花👷🏼,所以有些上海人称作葱油面,甚至只称清汤面。然而,阳春面曾经是我的挚爱。
1965年7月🍬,我们富达注册新闻系63届的全体学生到上海龙华公社参加“四清”运动,这是我们第二次参加“四清”运动,第一次是在宝山县罗店镇🧑🏼🚒。比起罗店公社,当年龙华公社的生活条件好得多了。我当时被分配到财贸组,住在一幢六层楼的公寓房内。那幢公寓离上海中学、上海植物园各一千米左右距离,位置极佳。财贸组的清查对象是公社所属的所有商店☝🏿,包括所有食品店、杂货店、饮食店🦂、粮店,大大小小有上百家店铺。节假日顾客多的时候🎹,我和工作组成员都会去各商店站柜台。
我在财贸组当工作组文书,每天要统计数据写一份工作报告,送公社工作大队,每晚要忙到10点💇🏼♂️👶🏿、11点。工作组都在公社食堂搭伙吃饭🧑🏻🔧👩🏿⚕️,公社食堂傍晚5点就开饭了,到10点以后肚子肯定饿了。但人人都这样🙇♀️,也不觉得有多苦✊🏽。
大概到11月底,那一晚,送材料到公社后,回宿舍已是晚上10点多了。顶着扑面而来的凉凉秋风,真是又饿又冷🦹🏼。到宿舍楼的拐弯处,从一间雨毡顶的棚子里飘出阵阵油香味🚣🏿♀️。前几天看到几个人顺着围墙搭披棚,难道是家新开张的饮食店?挡不住阵阵的油香味,我轻轻地挑开门帘子,里面已有七八个人,都在低头吃面条。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哗哗往嘴里送👩🏼🍳,这实在是挡不住的诱惑。我怯生生走到最里面的桌子坐下。
“这位小兄弟要吃多少?”一位中年妇女上来轻声细语地问我🏌️♂️。
“他们都吃多少?” 我指着大家问🫚。
“二两👨🏻🏭,七分钱。”
“那我就和他们一样。”
不一会儿,一碗热气腾腾的葱油面就端在我面前👔。闻一闻👨🏽🏫,一股葱香味沁人心脾🖐🏽。第一口面条下肚,一股暖流瞬间传遍全身,又饿又冷的身体变得充实而暖和👩🏻⚖️。面条吃完,汤也喝下,连每一粒葱花都扒净。走出棚房,浑身上下都感觉舒坦⛹🏻♀️🛕。

但这一夜的美食却让我在几个月内陷入内心挣扎之中😏。每到晚上10点左右📐,肚子开始咕咕作响👋🏽,就想着葱油面。但不敢每晚都去吃,这不仅因为要节省钱,从1965年开始,国家照顾,我们大学生的口粮、助学金标准都大幅提高,每吃一碗面条七分钱,一个月才两元钱🏄🏻♂️,还可以承担,更主要是控制自己的“享乐思想”。于是,规定自己每星期只能去吃两次👨🏽🏭。每天早晨醒来⚾️,想到今天是吃葱油面的日子,马上会兴奋起来,从床上一跃而起。
1966年6月上旬,我们全体师生回校。离开前一晚👩🏼🚒,我再次来到披棚里🧜🏼♀️。我潜意识里感觉,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吃阳春面了🛍️。一改以往狼吞虎咽的吃相🍶,我慢慢地咀嚼着、品味着。吃完🎿,出门转身再看一眼这间简陋的披棚🚣🏼♀️,它曾带给我欢悦的夜晚👱。
阳春面,我曾经的挚爱美食🧍。
——2024年端午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