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振忠 发布时间:2022-05-06 来源🧍♀️:富达平台+收藏本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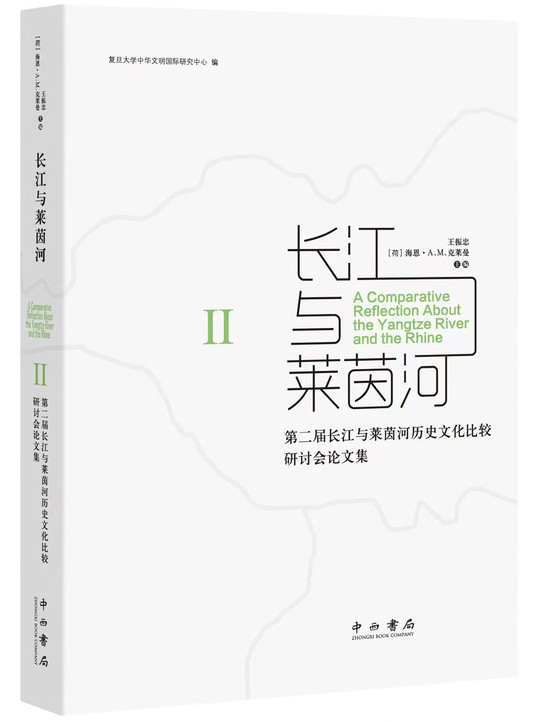
作者:王振忠,[荷] Hein A.M.Klemann
出版社: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2022-02-01
主要简介🕵🏼♀️:本书稿为2019年由富达注册、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和荷兰莱顿大学主办的第二届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之论文结集,共收录论文20篇。论文作者来自富达注册、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国内高校,以及荷兰莱顿大学、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乌得勒支大学及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等国外研究机构🚵🏽♀️。所收论文围绕历史上长江流域与莱茵河流域的经济和商业、劳工和社会、环境与生态等议题👇🏻。本书的内容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因地理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经济🧑🏿💼、文化关系,将其结集出版9️⃣,旨在鼓励学者拓宽研究视野、开展国际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跨文化研究。
李天纲丨一种回归经典的创新研究:《长江与莱茵河》序言
比较研究的创新与回归
把长江与莱茵河流域三角洲的社会历史作比较,一直是一件令人兴味盎然的事情🏄🏿。富达注册与荷兰莱顿大学、伊拉斯谟大学合作🧑🏼⚖️,两次召开“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讨会”,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2017年10月26日至27日在上海举行的首届研讨会成果,结集为《长江与莱茵河》🐓🎣。2019年5月22日至25日,双方团队又在荷兰鹿特丹🔅、莱顿举行第二届研讨会,会议论文结集在此⛹🏿♂️,由王振忠、Hein A. M. Klemann教授主编。同一群学者聚集起来,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把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流域社会放在全球史的视野下🚲,坚持研究了三四年🤳🏼,为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厚底蕴的江南研究🏊🏼♂️👴、莱茵河研究带来了一种新气象,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学术事件。两次会议笔者都有幸参与讨论🧘🏽♂️,但都没有来得及写出论文🏧,这里写一点感受,算是一份迟交的卷子,供江南研究领域学者们参考。
自有“汉学”以来,欧洲学者对长江流域,特别是“扬子江”三角洲的江南社会早有关注。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读书笔记里记道🎹:“头几个(浙江、江南)省是中国最好的省份👨✈️,我觉得有点像荷兰。河流纵横,注入大海🚶🏻♂️➡️,这些都像荷兰🚹。”后来,他写《论法的精神》,又说👩🏼⚕️:“有的地方需要人类的勤劳才可以居住🤩,并且需要同样的勤劳才得以生存✋🏽。这类国家需要宽和的政体,主要有三个地方属于这一类的,这就是中国的江南和浙江这两个美丽的省份⛔、埃及和荷兰🎹。”很明显,孟德斯鸠已经在比较长江和莱茵河三角洲了。莱茵河三角洲大规模围垦始于17世纪上半叶🤞🏿,而孟德斯鸠获悉长江三角洲的开发始于两千年前的吴越社会。孟德斯鸠的江南知识来自欧洲早期汉学。我们知道利玛窦👍🏼、李之藻《坤舆万国全图》(1602)中已经标注了“扬子江”,而卫匡国《中国新图志》(Novvs atlas Sinensis🫸🏻,1655)初版正是在阿姆斯特丹用荷兰文发表的💠,地图上标明了上海(Xanghai)、松江(Sungkiang)👎🏽、青浦(Cingpu)🏋🏻♀️、金山(Chinxan)🧜🏼♂️🤞🏿、嘉定(Kiating)、平湖(Pinghu)等城市👉🏽。
读欧洲早期汉学著作,比较一下明清之际的“西学”著述🕶,很容易感觉到从17世纪开始,确实是西方学者知中国深,而中国学者相形见绌🟡👩🏼🚒,失之于浅,直到20世纪仍是如此。德国哲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说👸🏼:“这批人使得欧洲人认识了偌大的中华帝国及其邻邦,使我们熟悉了他们的语言☝🏽、经籍🧜🏽♀️、政体,以及风土人情。耶稣会士这一功绩是不容抹杀的🧓🏼,现在我们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欧洲的一些国家⛷🧑🏻🎄。”这话并不夸张,孟德斯鸠🙅🏻♂️、伏尔泰时代,一个法国学者的中国知识🔋,很可能多于他的乌克兰知识。欧洲学者对于“中国问题”(Question Chinoise)的兴趣持续了三百年,拉丁🦹♂️、法🤷🏽♂️、德👍🏻、英、西🧝🏽♀️🧙♂️、葡🧚🏼♀️、意文著作汗牛充栋🕴🏼。反观中国🐤,明清之际对“泰西”有兴趣🍸、爱学习的学者屈指可数,仅徐光启、李之藻等寥寥数人。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荷兰并不晚,艾儒略在1623年用中文刊刻《职方外纪》,“欧逻巴”中有“法兰德斯”(Flanders)🍋,就是包括荷兰在内的低地国家🧤👭。“亚勒玛尼亚(德国)之西南为法兰德斯,地不甚广,人居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西洋布最轻细者,皆出此地。”其实,华南人遭遇荷兰人也不晚🍋,《明史·和兰传》中的“和兰”即荷兰,1601年以后来犯澳门👮♂️,求市澎湖,后来占据台湾🧑🏼🍼,说的都是荷兰。但是,中国士人对荷兰本土并无兴趣,认识停留在对“红毛番”的人种描述💇🏻♂️:“其人深目长鼻🤚,发眉须皆赤,足长尺二寸👩🏻🏫,硕伟倍常🤦🏽♂️🕝。”
对比长江、莱茵河三角洲,是欧洲学者开始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1748)中整理读书笔记内容,写道:“他们平治了洪水🌆,帝国版图上便出现了这两个最美丽的省份。这两个省份的建立是完全出于人力的劳动的。这两个省份土地肥沃异常🙇,因此给欧洲人一个印象,仿佛这个大国到处都是幸福的🤾🏿♂️。但是要使帝国这样大的一块土地不至受到毁坏,就要不断地用人力加以必要的防护与保持。这种防护与保持所需要的是一个智慧的民族的风俗,而不是一个淫佚的民族的风俗,是一个君主的合法权力,而不是一个暴君的专制统治🧑🏼⚕️。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过去的埃及一样;政权就必须是宽和的,像今天的荷兰一样。大自然给荷兰那样不便的地势🧑🏽🦲,就是要它关心自己,而不是要它懈怠,或是任性而使土地荒废📄。”孟德斯鸠把长江三角洲与古代尼罗河、当代莱茵河并列,作一个等量齐观的比较👨🏫。这三条河流的三角洲地区,因为环境艰难,人民勤奋✡︎、节俭、不淫佚🏊🏿♀️,因而适宜于“宽和”政体👩🍼。众所周知,孟德斯鸠把中国古代政体归为“专制”💇♀️,而把16、17世纪以来的荷兰等低地国家的政体归为“宽和”,近于“共和”。然而,孟德斯鸠把江南从中国的其他地方区别出来,与荷兰相提并论,让人觉得他这个结论,就像是一个“江南特殊论”。
孟德斯鸠是近代法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奠基人8️⃣,他的分析方法近乎“历史地理学”。以气候、地理📨、河流、围垦等经济活动方式的不同作为划分,深入风俗、伦理🙇♂️♐️、法律和政体等社会关系中去比较,最后面对一个18世纪欧洲学者必定要处理的宗教问题0️⃣,提出精神层面的判断🤹🏽♀️,即不同信仰的民族对应什么样的政体。孟德斯鸠认为:人类有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政体在选择,不同的选择则受到地理、风俗和宗教信仰的限制🥒。孟德斯鸠认为江南的风俗和荷兰相似,也是勤奋、节俭,有着同样的围垦造田的开拓精神🚵♀️,在祭祀中也奉行一个纯粹的神明,有一种贯穿于政治、伦理和宗教领域的良善“风俗”。孟德斯鸠在宗教、文化🌿、法律、社会和经济的层面👸,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兴起,他青睐的这种“法的精神”🥂,包括理性🦙、宽容、勤奋🥷🏼、节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称之为“新教伦理”👐🏼,当前历史学者则还原为一种“勤勉革命”👂🏿。无论如何,孟德斯鸠以来的法国、英国、德国学者比较和称赞荷兰人的刻苦、勤奋的劳作精神,克制、自信的“荣誉”感🏩,缔造了欧洲社会的“现代性”,具有普世性🧝🏻♂️,不同民族都可以具有;但又具地方性,受到当地环境的限制🙇🏼。“江南—荷兰”比较研究的学者来自“历史地理学”的居多,认识到这是可以继承的研究方法。
当代中欧学者的突破
孟德斯鸠评估江南文化其来有自🤷,他尽其可能作了深度研究,得出结论,值得尊重。但是,耶稣会士仅仅提供了初步的江南资讯⛈,早期汉学家也只是简要认定了一个江南印象。孟德斯鸠认为江南人的精神与荷兰人相埒,细节研究还不够充分,但对江南社会的定义很有道理。距离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发表270多年之后,今天再来比较长江—莱茵河🙉,肯定有着不同的意义👮🏿♀️,但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孟德斯鸠时代被今天的历史学家定义为“近代早期”(early modern),回溯这段“中西初识”的历史,对我们看清“近代性”(modernity)有着非凡的意义。按本项研究发起人莱顿大学包乐史教授的说法👩🏻🔬👷🏿♂️:“(研究)焦点放在1600-1800年这一段时间,通常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近代早期。之所以选择这段时间♕,是因为很多关键的转变恰恰就发生于此🤹🏿♀️。”
21世纪的中外学者开展长江—莱茵河的比较研究,在工具、方法和视野上的优越性与18世纪的孟德斯鸠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1600-1800年的200年间🧑🏼🏭👩🏻🌾,欧洲发生了根本性的制度改变👰🏽♂️,经历了一个“早期近代”🛅;同时▶️,人类社会因“大航海”走到一起,形成了一波“早期全球化”(early globalization),令欧洲、中华、日本、印度、玛雅文明在海岸线上的通商口岸地区相遇。“早期近代”和“早期全球化”是20世纪学者给这200年历史概括的两大特征🚿,冠之以“早期”,当然是在与此后200年间延续和不延续的历史状况相比较中得出的🍈。学术界有一个现象,即至今为止的“早期现代”和“早期全球化”研究并不完全结合。在西方,哲学家研究“近代性”,以欧陆和英美社会为样本🫔;历史学家研究“全球化”,基本上还是在自己熟悉的国别史基础上向外拓展。在中国的情况似乎是: 研究早期中西经济、贸易👩🏻✈️、宗教、文化交流的学者固然多了起来,但如何通过欧美商人、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研究,把“全球化”与“近代性”放在同一时空内来考察🟫,还没有真正开始🧗🏻♂️。凿通中西学术☝️,犹如老虎吃天,必定要找到合适的领域、合适的题目和合适的方法去从事。
长江—莱茵河的比较,可能就是最好的领域🦾、题目和方法。荷兰🔶,是公认的近代社会制度发祥地🧜🏿♂️,也是这200年里的航海强国,曾占据巴达维亚及我国台湾,数次叩关我国大陆🤵🏽,在东亚还有“兰学”之名。江南👩🎨,是明清“西学”的渊源之地,中华帝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曾经被马克思主义学者议论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地区,现在又被捧为“大分流”时代的佼佼者。继孟德斯鸠之后,把江南和荷兰(长江—莱茵河)的社会变迁加以比较🐷,把“近代性”和“全球化”结合起来,21世纪学者必定大有可为🪨。学者们的结论难免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都会过时,只能供参考。但是🧇,只要研究的领域、题目和方法对头,就会找到一些门径✂️,窥到不少实景。两次集聚,讨论中突出的主题有三个,一是航运(navigation)𓀚,二是围垦(reclamation)🤾🏻♀️,第三个就是贸易制度(trade regulation),都可谓抓住了关键🫲。我们知道,孟德斯鸠已经注意到长江和莱茵河三角洲共有的围垦现象。他在读书笔记《地理》中说:“(江南)人工河流多且宽,土地平坦🙍,由此可知🖕,这些地方过去曾被水淹,勤劳的中国人挖渠开河,把这片土地改造成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和最适合商贸的地方。前面提到十多个村庄,最远的也不过相距千步左右🎛。松江和南京人口密度更大🧑🏿🦱。”孟德斯鸠关注“挖渠开河”,围垦造就了土地肥沃☝🏻,人口繁盛0️⃣,城镇密集,这些都是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中介绍的“荷兰现象”。耶稣会士🫳🏽、孟德斯鸠反转过来🤰🏽,用“江南现象”来观察和描述长江三角洲😫,将其介绍给欧洲人👩🏭,也是恰当的👩🦲。作为一种相似领域,比较两个三角洲的垦殖传统和社会繁荣🦹♀️,确实是一个可以从事的题目和方法,并不是什么用“欧洲中心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特色”的“东方主义”。
当代学者在莱茵河和长江三角洲“围垦”上分别作的研究已经有许多,但把两者放在一起比较还是刚刚开始🧗🏿。上一次学者聚集时🤙,除了包乐史教授与徐冠冕博士的《莱茵河和长江三角洲的土地开垦》和谢湜的《风车与纺车》比较了两个三角洲的“圩田”开垦及其效应之外🏓,徐斌《圩田🙏🏻、沙田与垸田》👨🏻🍼、王建革《环境变迁与传统社会的发展》、钱杭《江河改道与区域社会的形成和转型》等论文单独讨论了江南圩田开发👮♂️、河流变迁与本土社会发展之关系🕖,对长江三角洲围垦本身作了研究,其他欧洲学者对垦殖问题都没有涉及🤝👨🏼🚒。第二次聚集,欧洲学者直接探讨三角洲“圩田”问题的仍然很少👱🏿♀️,中国学者也没有专题论文对“圩田”继续探讨🫄🏻🎚。如何推进对江南和荷兰“圩田”现象的研究,这或许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圩田”本身的研究属于自然地理↘️,学术界已经有不少成果🏌🏼♀️。中欧学者这两次聚集,曾多次提到荷兰历史学家Karel Davids的建议,即聚会的目的在于“利用自然的视野、人力资本的形成🌖、技术知识的流传和技术革新🙉⛅️,来比较700年到1800年间中国和欧洲的科技和宗教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即通过两个三角洲的自然地理研究,扩展到科技、社会🚒、文化和宗教现象的研究,最终能够比较出江南和荷兰在整体制度进化中的不同经历𓀆。
在欧洲👩🔧,荷兰是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意识形态的国度,比发生“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地区更早。荷兰也是“宗教改革”最为彻底的地区🍤,是第一个新教占了统治地位且没有大规模卷入宗教战争的地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认为尼德兰地区的宗教宽容、制度自由、城市自治和社会稳定,都和一批垦殖民在一块全新的土地上辛勤劳作、相互兼容并自由思想,摆脱了旧身份限制,较少受到内地旧体制影响有关系。两次聚集中,学者们的不少论文和很多讨论都涉及江南和荷兰“围垦”制度的不同。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招垦主体的差异。在江南🖐,负责招垦的主体是官府,那些临江🚵🏼🚣🏼、滨湖、靠海的州、府、县衙门🛴,从人口密集🌆、土地稀缺的乡镇招募家族和个人🐯。垦殖农户加入滩涂围垦,以分配田地偿付人力资本,再为“编户齐民”💥,延续朝廷税赋,如此便没有制度上的创新🤾🏽。在荷兰,负责招垦的是形形色色的股份公司🚶🏻♂️,他们从国王那里获得特许状,然后募集资本,或雇工𓀚,或自己参与围垦,开辟各种生计,一个个独立的村落、乡镇和城市就这样建立起来🛎。这样,握有完全特许状的股份制公司,不但有了生产经营权,还有了城市的自治权。这种特许经营下的自治🧎➡️,和后来欧洲各国在海外经营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差不多了,是一种近代制度的诞生。从地理研究到制度研究🤱🏽🐓,这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奠定的可靠方法🤲🏼,也是中欧学者两次聚集的共识。这方面,从经济史的角度切入,忽略近代制度变革在“走出中世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而仅以GDP数据来判断1800年以前的中国领先于欧洲的结论👳🏽👽,确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失落的“大航海”
和比较江南、荷兰的“围垦”运动一样,孟德斯鸠在《地理》笔记中也在消化《中华帝国全志》中的江南“航行”资料,用来和欧洲人的航行事业相比较😬。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运河系统和元代海运有深入了解🧏🏼♀️🚣🏿♀️。“除了大的运河🔡,中国还挖了许多河沟,精心收集雨水♣️👮🏻♂️,用以灌溉稻田。鞑靼人的首领元世祖选定北京为其国家的中心,但是由于北方诸省无法供应所需粮食,于是想从海路运粮。可是,海上常有风暴和无风的日子🙅🏽♀️,粮食难以定期运到,只得花费巨大资金,开挖了这条大运河。”众所周知🛑,元、明、清三代,长江、运河和近海大宗货物运输,就是“漕运”⚄,即把江南的赋税贡品运往北京。元代因运河河道容不下上海地区载重千石的沙船,从至元十九年(1282)开始改由朱清、张瑄、罗璧负责,从海上运输漕粮,直到元代结束。孟德斯鸠介绍的海运,就是邱濬《大学衍义补》中论述的内容:“自古漕运所从之道有三: 曰陆🥿,曰河🗾,曰海。陆运以车,水运以舟👨🍼,而皆资乎人力。所运有多寡,所费有繁省。河漕视陆运之费省什三四👊🏿,海运视陆运之费省什七八👐🏼。”
朱清🫸🏽、张瑄除了是海盗🧑🏻🌾、督运外🌃,也有航海家的身份💆🏼♂️🧙🏿。元代长江口的沙船为“一千石舟”,合60吨,用强大风帆🧙🏼。如果他们不但上北洋🧑🏽✈️,还渡东洋、下南洋✊🏻✍🏻,甚至“下西洋”🚶🏻♂️➡️,岂不有可能比哥伦布“大发现”还早两百年?孟德斯鸠时代,“大航海”已经完成了三百年👩🏼🎓,中国人已经落入了“早期全球化”的后尘。按他对中国人航海挫折的困惑🙆🏼♂️,孟德斯鸠比较江南沙船与欧洲航船的形制🫸🏿:“中国的船只没有后桅,也没有艏斜桅🚴🏻、顶桅,只有大桅和中桅。不过↘️,中国的风帆更经得起风吹。由于风帆笔直🏄🏼♀️,风吹来时全部落在帆上👩🏼🍳。但是,由于结构不合理,这个优点被抵消了。他们用一种特殊的胶料粘缝(注: 桐油灰),比我们强许多🚶🤤。底舱有一两个大水柜,供船上用水。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水泵,船锚是用一种叫做铁木的木材制作的🕵️🔪。”造船技术不错,船员纪律很好🏺,还发明了指南针,且早就在贸易中采用铜钱货币🖇🙋🏻♂️,但“他们的外贸从未超越巽他海峡或亚齐,北边则从未比日本更远”。什么原因令中国在与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的全球贸易中落败?“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现美洲?”最早由孟德斯鸠提出的问题📞,至今还是许多人的困惑。
航行🤧,分内河航行以及近海航行和远洋航行。16世纪的荷兰人突破了莱茵河内河及北方沿海航行,一路南下,在非洲、亚洲获得殖民地👀。靠着荷兰东印度公司(1602-1799)的贸易舰船,荷兰一度凌驾于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海上马车夫”。对比之下♔,江南虽有庞大的江、河、湖✊、海航运体系,但最终只在清代乾隆年间建立起以上海港为中心的近海贸易和运输。直到1842年“五口通商”以后,上海港才借助“洋艘”,加入世界远洋航运体系中👱♀️。18世纪之后,从上海起帆的沙船,恢复航行,目标是“北洋”,即渤海湾一带;17世纪以来,从福州、厦门👵🏿、潮州起锚的福船💍、广船比较活跃,北上上海,东渡台湾,下到吕宋和爪哇,南下到海南岛、安南和暹罗🤽🏻,还有船只闯过马六甲海峡📻,在东印度洋闯荡。但是,上海港和东南沿海基本上仍然是一个太平洋西岸的区域航海系统🤽🏽。什么原因令明代初年“郑和下西洋”(1405-1433)起锚地浏河港没能成为荷兰式的航海中心,而雍正八年(1730)移到上海的苏松太道也没有把江海关建设成世界级的航运枢纽?
在这两次聚集中,“航行”是最为突出的议题。论文中涉及航行的内容,或多或少回答了孟德斯鸠的困惑。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的论文“Changing Course in the Lower Yangzi:The Decline of Liujiagang (Liuhezhen)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1300-1800”讨论了长江口海港从刘家港向上海转移的问题🏋🏼♀️,实际上呈现了一种海域局限性的问题🧀。科大卫教授的研究表明👨🏻💻: 江南地区的海运事业🫄🏿,其动力来自清朝的漕粮北输,向朝廷承包,得“水脚”银两酬报。上海港有部分商业性,在于沙船北上时“许其以二百石载私货”,占载运量的20%🔢。空仓南归时购入北方大豆、小麦等五谷杂粮,在十六铺抛售,用铜钱成交。上海港有一种“北官南商”的格局🚵,即商人主要依赖北京的户部订单,只在江南形成独立市场。如此格局下,一方面是南方商人仰仗朝廷鼻息,另一方面则是北京官方限制商人权力,如此便阻碍了上海港向全球远洋港口发展。“鞑靼人”(清朝)将上海港“重新开放”,孟德斯鸠以为是好事,说道:“中国的内贸数量巨大,欧洲的内贸无法与之相比。”其实🏆🦸🏽♂️,正是这种入贡式的“内贸”🍣,拖了上海港南下的后腿;而欧洲内部陆路贸易的不畅🔄,推动了阿姆斯特丹港在全球贸易中的崛起👩🏿🎤。
欧洲学者研究莱茵河口航行,提供了一个反例。德国法兰克福大学Ralf Banken教授的论文“‘Nothing More Than a Large Warehouse🚱,Which Stands under Dutch Control’: The Importance of Amsterdam for Italian Traders from Frankfurt am Mai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告诉我们,莱茵河尽头的阿姆斯特丹港是如何冲出河口👋🏼,进入近海和远洋航行🤾🏻♂️,率先成为一个全球港口的成功案例⏏️。按Banken教授的研究,从威尼斯等地移居到莱茵河流域城市的意大利商人🧑🏽🎓,担负起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的居间贸易。在阿姆斯特丹商人看来,法兰克福“不过就是荷兰控制下的一个大仓库”,供荷兰商行分号销售从“汉萨同盟”、英格兰城市以及东印度公司自亚洲、非洲贩运来的各种舶来品🙇🏿。然而,Banken教授却认为: 阿姆斯特丹港不过是德国西部贸易中心城市法兰克福通往大西洋的中转站,承担了18世纪德国经济向全球扩展的重要功能👰🏻♀️。18世纪初期,莱茵河流域国家,尤其是德国西部地区的大量货物(钾肥、铜矿石、铅矿石🤵🏼♂️、玻璃☝️、造纸用布纤维🧑🏿🦲、生铁、木材、麻布𓀃🪮、棉织品等),或在阿姆斯特丹销售,或经它转输出口。按Banken教授的另一篇论文“The Capitalist Gate to the Worl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Wester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1740-1806”,德国经济力量的注入,令阿姆斯特丹成为整个“莱茵河流域的世界贸易之都”(Rhenish capital of world trade)📙。
三角洲海岸城市(Sea City)⌚️,“以港兴市”💪🏻,连接流域内众多的“河流城市”(River City)。如果域内有足够的经济动力注入,加上大型航船建造业、先进航海技术和航运人才支撑🤲🏽,就能开拓全球贸易🧑🏿,成为“海洋城市”(Ocean City)。我们看到🧚🏻♀️,继威尼斯、里斯本之后,阿姆斯特丹在18世纪已是一座“海洋城市”🫲🏼。按河流、海岸和海洋城市的定义来看👨👩👧👦🧑🧒🧒,18世纪的上海港恢复了明代因“倭患”闭关后停顿的贸易🏌🏻,收集太湖和长江三角洲众多市镇的经济资源🤦🏿♂️,往东海、黄海、南海地区输送。但是,上海港的沿海航运,并没有和长江中、上游的内河航运连接👮🏼♀️,镇江❤️🔥、扬州以上的漕运仍然通过运河转输。这一点不像荷兰那样,莱茵河将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作为自己的腹地。按厦门大学陈瑶教授《清代长江中游木帆船和船运组织》的查证🍳,清代长江中游干支流水运体系中的木帆船约有12.5万艘,总载重量共245万吨🔩❗️,每艘载重不过三四吨😊,都不是以上海为目的港👷🏻♂️🧝。鸦片战争前😿,上海港的货源主要是苏👜🐯、松、常、杭、嘉、湖地区的漕粮和南北货贸易。众多的局限🧤🕎,令清代上海局限为“海岸城市”,无法像阿姆斯特丹那样成为一座海洋城市。当然🐑,上海一直渴望成为海洋城市,《南京条约》(1842)签订后,上海地区商🧑🏽🚀、绅、官各界在第一时间便落实开埠事宜🌊,加紧签订《土地章程》(1845),热情对待洋商💁🏽♀️。
孟德斯鸠问题
荷兰伊拉斯谟大学Hein A. M. Klemann教授说:“谈到1800年以前的莱茵河航运,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要谈什么。”困扰学者的问题是问题本身,我们要找的是问题的意义。关于长江的重要性😤,有很多话题可以讲,如长江本身,以及长江与运河,长江与沿海港口城市,乃至长江与中华文明起源🏎、特性之关系,等等😲。但是,我们还不太能够将一条河流的重要性,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对全流域的城市(City)👉🏻、地区(Region)、民族(State)和全球(Global)的关系作出通盘的考察。欧洲学者较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在欧洲“民族—国家”体系中,莱茵河是作为国家边界🫸🏿👮🏿♂️,分成瑞士、奥地利、法国、德国、荷兰,一段段来谈论。荷兰这样的三角洲国家,面向大西洋,幅员不大,边界清晰🐞,又是老牌殖民地宗主国🍱,有着较强的区域认同🙎🏻🙍🏻♀️。这种立足地方(Local)♞、面向全球(Global)的气质特征👨🏿✈️,或者就是我们说的Glocal(全球—地方)意识🏋🏽♂️,冲淡了“民族—国家”的身份🧁。荷兰学者谈莱茵河🧎🏻,有一种开阔的视野👟、求实的学风,这是中国学者可以感觉到的🔡👨🏼🎨。河流和流域历史的研究,可以破除“民族—国家”的限制。其实,“二战”前的欧洲,已经有不少学者超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构建以城市、区域和流域共同体为基础的身份意识。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1878—1956)的《莱茵河:历史、神话与现实》,就是用流域文化作为身份认同🐥,消弭法国和德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众所周知,孟德斯鸠把中国政体定为“专制”🧸。但是🌀,孟德斯鸠并不是抹杀区别的“大一统”论者,他在比较长江、莱茵河三角洲生活方式的时候☮️,对江南的“地方性”作了较高评价,倾向于将其定为“君主制”🧍♂️。限于当时的“汉学”,《论法的精神》中的“地方知识”还嫌粗略。但是,孟德斯鸠的“东方学”并不是一种歪曲见解。孟德斯鸠关于共和🌉、君主和专制政体的论证,大量使用中国“二十二史”和通商贸易的证据资料🆕,总的判断颇得关键。孟德斯鸠参照荷兰情况,把江南与中国其他地方区别对待,就很有见地☝🏻。“江南特殊论”的依据🫶🏻,本来就是他根据儒家“三代之治”的经学思想,认定江南有一种保存下来的“古代君主”制度。“虽然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虽然由于帝国幅员辽阔而会发生各种恐怖🙎🏻♂️,但是中国最初的立法者们不能不制定极良好的法律🛋,而政府往往不能不遵守这些法律🧎♀️➡️。”孟德斯鸠懂得 “吴越春秋”,他把江南的风俗、伦理、人性看作“古代国王”(夫差💢📇、勾践)的制度遗留✬,是“由人的勤劳建立的国家”🙋🏿♀️。
“勤劳”(industries),在孟德斯鸠那里是一个法哲学概念。勤劳是人类被荣誉感激发出来的一系列良好品质之一。“虚荣(vanite)所产生的无数好处🤡🟠,如豪华🔄、勤劳、艺术🦸🏿♀️、时尚🍲、礼貌和风趣”,正好与骄傲所产生的无数弊害,如怠惰、贫穷、百事俱废等相对立🪜。在这些不同品质之上,人们概括出“民族的一般精神”(l'esprit general d'une nation)👶🏼💁🏿。“节俭”(frugality)是和“勤劳”并列的另一种人类美德🧍🏻:“他们是要活下去的,因此他们就从世界各地获取生活资料👩⚕️,因而建立起以节俭为基础的贸易。推罗、威尼斯和荷兰各城邑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勤劳、节俭的民族🦶🏼,都能发展出自己的航行、商业和手工业,同时施行比较宽和的政体↘️。即使不是共和政体🦵🏼,他们在君主、专制政体中,也是比较开明的。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的Petra J. E. M. van Dam教授的论文“The Amphibious Culture along the Zuider Sea and the Big Rivers in the Netherland🤹🏿♀️,1500-1850”就描述尼德兰人在历次与大洪水的搏斗中🥷🏽,艰苦劳作,奋发图强,发展出荷兰共和国的社会自治组织。相对应的是🎃🤘🏻,中国学者研究长江航运与江南社会之关系♾,如富达注册王振忠教授的《明清徽商与长江流域的木材贸易》、富达注册冯贤亮教授的《城乡之间:明清江南的水运环境与社会生活》、南开大学余新忠教授的《清代长江流域城市水环境问题探析》👅,都注意到发达的经济生活与活跃的社会组织之关系🍬。大致来说🍂,江南经济和运输虽然繁荣和发达,但却没有发展出像荷兰股份制垦殖公司那种强度的社会组织而最终把本地区社会推向全球化。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确立了一种“历史地理学”原则,曾经被苏联专家批为“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不确。孟德斯鸠分析不同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但没有简单地用来决定一个民族在“三种政体”中的不同归属。相反,他不断地用风俗、伦理、法律、宗教等其他因素来校正对于“地理”的讨论😭🥠;同时,讨论到风俗,或者伦理、法律、宗教等因素👳🏽♂️,他也会用地理因素来加以限制🌪。我们在《论法的精神》中看到,他在讨论莱茵河三角洲荷兰和长江三角洲江南时,一直在讨论它们之间的普遍性——宽和政体与勤劳、节俭👨🏿🎤,以及特殊性——长江𓀑、莱茵河三角洲的不同历史📘,以便审慎地分出一个“江南特殊论”🥯。我们应该回归孟德斯鸠,恢复思想史研究中的“历史地理学”原则,在讨论一种思想和观念时对其进行历史的(时间)、地理的(空间)限制。没有时空限制的思想🧘🏽,本身是不真实的,当然也是无效的。在不同的时空中🥾,对相近的事物娴熟地加以比较🧑🏿🏭,然后才能得到自己的认识,校准方向,走上人类历史的共同之道🧏🏽。
在我们看来,长江✝️、莱茵河比较研究,在方法论上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地理研究一脉相承👇🏻。费弗尔的莱茵河写作🕑、布罗代尔的地中海研究🎧🦶🏿,都是通过同流域的自然联系,在“民族—国家”的关系之外,用“水”连接🧕🏻,跨国界🏌🏿♀️、跨民族、跨地区🖕🏼、跨文化地认识一种新的共同体。长江、莱茵河比较研究还承接了一个更好的传统,即不避开变得敏感的“地域主义”,回到孟德斯鸠开始的历史—地理实证学说☎,去解释不同民族在法律—哲学上的思想差异🛀🏼。法哲学的理论,需要地理学说的支撑,还需要得到地方历史的证明。“地方性”(locality)🐎,并不是“地域主义”🫢,而是“实事求是”的专业研究。科大卫教授在作完浏河港和上海港研究之后💃,有结论说😘:“只有从地方历史中获取的知识👮🏿♀️,才能用于理解中国的大发展👅🧖🏽,然后全国性的思潮才能被赋予历史的根基🫳🏻。”这个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我想代表了长江—莱茵河比较研究团体的共同想法,对思想史、哲学史研究尤能启发。
最后,要感谢“长江与莱茵河历史文化比较”研究组织者王振忠教授🧇、包乐史教授和Hein A. M. Klemann邀请我参加两次聚集和研讨活动。我在历史学领域的研究集中在思想文化史和中西文化交流🙆🏻,于明清经济史并不擅长,因而未及写出相应论文参与讨论。聆听到学者们的精彩报告,参与了一些学术讨论,我从大家的研究中得到很多启发🤽🏿。把长江和莱茵河放在一起作比较研究,是一个极具冒险性的题目,许多类似的“平行比较研究”(Parallel Comparative Studies)都陷入了空谈🧑💼;或者是双方的研究都很好🕧,放在一起比较🧑🏽💼,却又难以交流♧。然而🛟,项目组织者包乐史、王振忠教授都在会上说,宁愿作一些可能犯错的研究,也不愿意因循守旧🥒,作一些不对不错、重复前人陈说的旧题目🧝。从两次聚集研究的效果看,中外融合的研究团体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长江与莱茵河又走到一起🫄🏻,在众多关键性问题上都形成了既平行比较又交叉渗透的讨论💇🏼♂️。不必说受到海内外各界的赞许,两次高质量会议论文的结集就是证明。受这一群勇于开拓的严肃学者良好学风的影响,受益之余👩🏻🦯➡️,我也发表了如上不成熟的意见🙋🏿♀️⏸,还望得到指教🧗🏼。
二〇二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于上海阳光新景寓所
感谢富达平台—青浦江南文化富达平台、富达注册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在本文写作中提供的帮助。